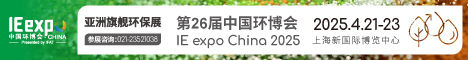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核事业健康发展
(190).jpg)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8月28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对《核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三审稿进行了分组审议。
在审议《草案》时,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代表普遍认为,为保障核安全,预防和应对核事故,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推动核事业健康发展,制定核安全法是必要的。
《草案》总结了我国核安全工作实践经验,按照从高从严的要求,对核设施选址、设计、建造、运行、退役和核材料及相关放射性废物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的监管和风险管控,符合核安全工作实际,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代表、委员们对《草案》三审稿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细化涉核项目选址的决策程序
甘道明代表建议,进一步突出对法律关系的调整作用。适当精简有关纯科学技术、具体技术标准、流程规范的内容,高度聚焦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违法责任、法律程序等法律范畴的问题,尤其是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明确基本的选址原则,将公众安全和环境治理作为硬性标准,并设置听证程序,赋予公众更多了解情况和表达意见的权利。
同时,建议《草案》进一步细化有关涉核项目选址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内容,明确选址的基本原则和程序。涉核项目选址决策前应当依法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安全性评估与检测,用以预防核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在涉核项目预选址过程中设置公众参与的机制和程序,充分保障公众在涉核项目选址上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进一步完善核损害赔偿条款
方新委员说,《草案》中核损害赔偿写得不够。核损害赔偿制度应该是核安全法的重要内容,也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内容。现在只是在第十一条第二款写了“受到核损害的,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在第八十九条作了一个相应的规定,但是有关规定写得不够。
因为核损害的特殊性,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在相关的法律中,引入了一些不同于一般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比如说严格责任原则、唯一责任原则、有限责任原则、责任豁免原则等。这次的修改对责任豁免基本谈清楚了,但是对于严格赔偿责任谈得不够。特别是第八十九条第三款关于赔偿制度的规定不到位。
从其他国家的法律看,核损害赔偿制度第一是企业要有自己的财务保证金,设立损害赔偿基金;第二要有强制责任保险;第三要有政府兜底的原则。
第八十九条只是写到企业应当通过投保责任险和参加互助机制,显然不够。建议对这条再做斟酌,明确核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要点,例如设立损害赔偿基金、强制责任保险和国家兜底责任等内容。
刘振来委员说,第八十九条讲到“因核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损害的,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核损害责任制度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武装冲突、暴乱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除外”。“除外”中讲的几种情形,造成的核损害不予赔偿。但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在表述上有缺陷,不够严谨。
如果战争、武装冲突是由敌对国挑起的,使用了含有核材料的武器,造成了严重的核损害。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对施害的敌对国提出核损失赔偿的要求,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对国家和公民来说也是必需的。
现在《草案》做出“除外”的规定,在发生涉外的上述核损害赔偿问题时如何处置,应该予以认真考虑。在法律条文当中不要因为“除外”的规定,在法律层面上留下漏洞,对将来处理涉外核损失赔偿问题以及我们的政治外交斗争造成不必要的被动。
黄献中委员说,对第八十九条提一点修改意见,“因核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损害的,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核损害责任制度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一句“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武装冲突、暴乱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除外”。这句话从法律的严密性来讲,还值得探讨,故意造成核设施事故的是重大的犯罪行为,对这个责任的主体还存在赔偿问题吗?对它是实施法律的严惩问题。
另外,造成了核设施事故,它造成的危害绝不可能仅仅是对受害人本人的危害,对设施的损害、对其他人员的伤亡赔偿不赔偿?前面也讲到了核设施运营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问题,即使是所谓的受害人,实际上也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他(她)有意地破坏核设施,恰恰是因为核设施运营管理单位管理不善,造成了被破坏的可能,管理单位的人员也应当受到惩处。
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
缪蒂生代表说,对违反第七十四条的,谁来处理,没有明确的部门。除了第五项情形是按照国家保密法来处理,第六项情形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按照刑法来处理,其他事项由什么部门处理不明确,应该归档的没归档,应该信息公开的没公开,依法怎么来处理,谁来处理还不明确。
第八十五条讲了六种情形,但这六种情形的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都用罚款,有的仅仅是处以5万元的罚款,这个处罚太轻了,根据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国家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总趋势,如果这个法律定下来,制定这么一个处罚标准,六种情形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处罚,对于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市不够的。总体的处理都是罚款,有的就是两万元,最高也就200万元,应该从处理上分清轻重,特别是核方面如果造成危害,仅仅处以两万元,处罚的法律后果太轻了。
林笑云代表认为,《草案》有关惩罚标准偏低。核安全这么重要的事,罚款罚得这么低,例如第八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受委托的技术支持单位出具虚假技术评价结论的”,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最后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同时直接责任人只罚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偏轻。
刘占芳代表认为,核安全这个事情,一定要把门槛设得更高。法律责任不应该用钱衡量,还应该有刑事处罚,但是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确门槛太低。首先要从法律上提高门槛。如果出问题则是影响深远的灾难性问题。既然制定了这部法,就一定要让它有威慑作用,有震慑力。关于罚款的问题,现在提到罚款20万元,这不是数字的问题,应该把参与单位,像营运、材料、运输等单位罚得倾家荡产,否则震慑作用不大,也不利于国家核安全管理和核能经济的健康发展。
核安全相关管理机构缺少统筹部门
王毅委员说,《草案》第六条对核安全相关管理机构的职能进行了规定,但缺少统筹部门,一旦出现问题,容易出现推卸责任和扯皮现象,建议将第一款改为“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统筹核安全的监督管理”。
另外,这一条的第三款提出“建立核安全协调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缺少具体规定,鉴于后文中第五十条提到“协调乏燃料运输管理”、第五十三条规定“设立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建议把这一款第二句话改为“统筹协调乏燃料处理处置及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草案》第十条规定了加强核安全相关研究完全必要,但在第二款中规定过于具体,也容易挂一漏万,建议把这一款第一句话改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相关科研规划中安排核安全关键技术研究专项”。
姒健敏委员说,《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设施关闭以后安全监管措施,还要加一条兜底条款,即关闭的设施移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进行监管后,补充“不得利用开发”的内容,否则移交给当地地方政府监管后,当地以为已经安全了,就有冲动重新开发利用,则有可能出现安全漏洞。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